喜迎!中国最强地级市 正在拼命建大学 “国字号”坐落江苏,目前江苏在校大学生约30.4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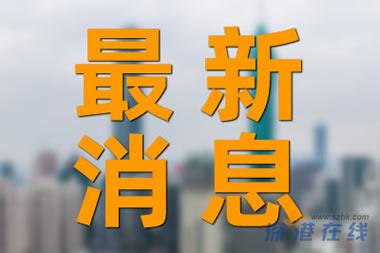
中国最强地级市 正在拼命建大学
【中国最强地级市 正在拼命建大学】2025年11月20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公示,拟按程序向教育部申报设立中国中医科学院大学(暂名),办学地点为江苏苏州。这座被称为“最强地级市”的城市,由此迎来首所“国”字号大学。消息一出,舆论再次聚焦一个正在发生的趋势:一批非省会经济强市——深圳、青岛、东莞、佛山、无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补齐高教短板,重塑城市创新版图。苏州的“大学故事”,是一部产业与科教相互成就的现实样本。过去十余年,苏州以“引进大院大所”开路,先后集聚清华、中科大、西安交大、浙大、上海交大、复旦、哈工大等20多所985高校的研究院,形成“研究院之城”的先发优势。但研究院多偏科研与研究生培养,本科体系与完整大学建制不足,成为城市高教版图的明显短板。转折发生在2021年:苏州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签署共建协议,确定在吴中区临湖建设“中国中医科学院大学”。此后,项目加速推进:2022年选址与开工,2023年东区主体封顶,2024年东区首期交付,2025年4月东区全面竣工交付。此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示明确:建校基础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举办者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类型为普通本科、性质为公办,办学地点在苏州。校园规划用地约610亩、总建筑面积约32万平方米,以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中药学为主干学科,规划在校生约5000人(含留学生约500人),直属附属医院为苏州市中医医院与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这意味着苏州不仅补上了“本科大学”的缺环,更以“国家队”平台切入中医药高端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的核心赛道。
苏州的选择,折射出非省会经济强市的共同逻辑:经济与产业能级跃升之后,高等教育成为制约创新与人才供给的关键短板。以数据观之:深圳在校大学生约20万人,不足省会广州的1/8;苏州在校大学生约30.4万人,不足省会南京的1/3。过去,这些城市可以凭借产业与薪酬优势“虹吸”全国毕业生;但当人口与产业竞争进入存量博弈阶段,“抢人”之外更要“育人”,自建高质量大学成为必选项。
更重要的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对高学历、复合型人才的渴求前所未有。以2025年“两院”院士增选为例,新增院士中来自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占比极高,显示出“科教—人才—创新”链条的决定性作用。苏州在生物医药、高端制造、新材料等领域集聚度高,对“从0到1”与“从1到N”的贯通式创新生态要求迫切,建设高水平大学,正是补齐“源头创新”与“人才蓄水池”的关键抓手。
苏州的突破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还在于“国字号”大学之稀缺。依据教育部2020年印发的《高等学校命名暂行办法》,高校名称原则上不得冠以“中华”“中国”“国家”“国际”等字样,也不得冠以“华北”“华东”“东北”“西南”等大区字样。这使得新设高校多以所在地或学科领域命名,如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福建福耀科技大学等。在这一制度背景下,中国中医科学院大学的设立路径具有特殊性:其建校基础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举办者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属于服务国家战略与行业需求的重大布局,因而获得“国字号”命名空间。这也解释了为何“国字号”高校长期集中于北京等历史形成中心,而新设大学鲜见“中国”前缀。苏州的“破局”,既是城市能级与产业实力的体现,也是国家层面优化高教布局、服务区域创新体系的成果。
苏州并非孤例。深圳在过去十余年几乎以每年新增一所高校的速度推进高教跨越: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跻身全球高校500强,哈工大(深圳)、中山大学(深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录取分数与科研影响力齐升,形成高层次人才的“蓄水池”。青岛迎来全国首所以“康复”命名的康复大学;东莞的大湾区大学与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获批筹建,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政策环境对“如何建大学”也在塑形。一方面,“禁止重点高校跨省异地办学”持续收紧,倒逼地方走“省内分校、中外合作、本土新建”的路径;另一方面,中外合作办学与新型工科大学成为突破口。苏州在此方面的组合拳颇具代表性:一方面引入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设立校区,另一方面与英国萨里大学共建“苏州萨里大学(筹)”,定位为立足中国实践、服务产业发展、链接全球资源的新型工科大学,聚焦先进制造、未来能源、智慧健康等前沿方向,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试验田”。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非省会城市并非没有“逆袭”样本。四川宜宾以“大学城+创新城”双轮驱动,不到十年集聚10万名大学生、12所高校、15所产研院、2家院士工作站,依托宁德时代等龙头形成动力电池全产业链,构建“头雁引领—雁阵齐飞”的产教融合生态。其核心经验在于:以政策组合拳快速完善城市功能与载体,以龙头企业牵引创新链条,以平台化组织打通“产学研用”闭环,最终实现人才与产业的同频共振。
城市“拼命建大学”,但真正的考验在于“建什么样的大学、如何建”。从现实看,至少面临三重挑战:
• 第一,定位与同质化风险。新型大学容易陷入“大而全”的冲动,忽视城市禀赋与产业需求。对策在于“小而精、专而强”,围绕1—2个主干学科打造高峰,形成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苏州以中医药为突破口,深圳以新工科与交叉学科为牵引,皆是“以特制胜”的体现。
• 第二,体制机制与治理能力。高水平大学需要学术自治、评价改革、交叉融合的制度供给。应建立以质量与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鼓励PI制、跨学科中心、产业联合实验室等组织创新,打通“从论文到产品”的最后一公里。
• 第三,产教融合的可持续。大学不是“孤岛”,必须与龙头企业、产业园区、地方政府形成共生关系。可借鉴宜宾经验,构建“院士工作站—产教联盟—共享仪器平台—联合培养”的立体生态,让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同向发力。
此外,还需警惕“大学泡沫”与“唯指标论”。大学建设是长周期、慢变量的系统工程,不能简单以论文数、帽子数、项目数替代真实贡献。对城市而言,衡量大学成效的关键指标,应是本地产业创新能力提升、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毕业生留本地比例与城市创新生态的活跃度。
从苏州到深圳,从青岛到宁波,非省会经济强市正在用一座座新大学,改写中国高等教育的地理版图。它们的路径各不相同,但底层逻辑高度一致:以高质量高等教育支撑高质量创新,以人才密度提升产业能级,以制度供给激活科教融合。中国中医科学院大学的落地,是苏州的里程碑,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布局优化的注脚。它告诉我们:在“国字号”稀缺的时代,真正的竞争力不在于名字,而在于能否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城市产业场景为依托,以高水平人才为核心,构建面向未来的创新生态。这既是苏州的答案,也是所有经济强市的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