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做手术时手机因“涉诈”被停机 二十多天无法与病患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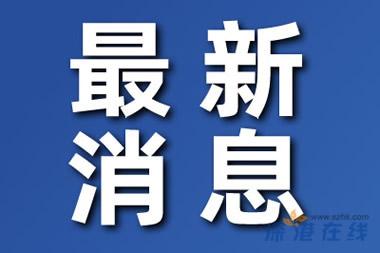
医生做手术时手机因“涉诈”被停机
【医生做手术时手机因“涉诈”被停机】近日,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某医院手术室内,主刀医生杨先生的手术刀悬在半空——监护仪发出刺耳警报,患者血压骤降,急需联系血库调配稀有血型。然而,他摸向白大褂口袋的手机,屏幕漆黑一片,一条短信赫然显示:"您的号码因涉嫌电信诈骗已被暂停服务。"这场因反诈风控引发的医疗危机,将技术治理与人性温度的冲突推至风口浪尖。10月12日上午9时17分,正在进行肝胆外科手术的杨先生遭遇突发状况:患者术中出血量骤增,需紧急调用Rh阴性血。当他按下手机拨号键时,屏幕突然弹出"涉诈停机"提示。这台承载着生命通道功能的手机,就此沦为一块冰冷的金属板。
"当时手术室里的空气都凝固了。"参与手术的护士回忆,杨先生不得不中断手术,通过医院固定电话联系血库,导致关键救治环节延误7分钟。所幸患者最终脱离危险,但这场惊魂时刻揭开了反诈系统与医疗场景的深层矛盾。
杨先生的妻子杨女士同样陷入困境。作为同院内科医生,她的手机在丈夫号码停机后预留为申诉联系方式,却在次日因"使用异常"被同步关停。"我当天打了23个电话跟进患者病情,就被系统判定为涉诈风险?"杨女士展示的通话记录显示,其日均通话量达47次,远超普通用户。
这场"数字断联"持续26天。中国移动要求机主携带无犯罪证明前往号码归属地长沙办理复机,而沅陵县营业厅以"异地号码无权处理"为由拒绝受理。更讽刺的是,当杨女士通过公安平台开具电子证明后,系统仍以"需线下核验"为由拒绝线上复通。
中国移动客服给出的停机理由存在多重版本:初期称"通话频率异常",后改口为"终端异动模型触发",最终归结为"系统自动识别涉诈风险"。这种解释的模糊性,折射出反诈技术治理的深层困境。
据运营商内部人士透露,当前反诈系统主要监测四大异常行为:①单日拨打陌生号码超50次;②新办卡长期静默后突然高频使用;③号码使用轨迹与登记信息不符;④终端设备更换频繁。杨女士夫妇的遭遇恰好触发多项规则:医生职业特性导致的高频通话、跨区域执业引发的定位异常、医院公用电话导致的设备切换,均被系统判定为"高风险行为"。
"这就像用筛子捞鱼,连小鱼苗都被捞走了。"网络安全专家李明指出,当前反诈模型采用"宁错杀,不放过"的粗放策略,缺乏对特殊职业的差异化识别。他展示的某运营商风控系统截图显示,医疗、教育、物流等高频通信行业被标注为"涉诈重灾区",其用户触发停机的概率是普通用户的3.7倍。
这种技术治理的"一刀切",正在制造新的社会矛盾。新疆乌鲁木齐的张先生因工作调动频繁跨省,手机在半年内被强制停机4次;贵州贵阳的王女士作为社区志愿者,日均联系居民200余户,号码被标注"疑似营销诈骗"……当反诈技术沦为"宁枉勿纵"的数字枷锁,公众对技术治理的信任正在悄然流失。
这场风波暴露的反诈治理困境,本质上是公共安全与个体权益的价值排序问题。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十一条,运营商有权对异常号码采取限制措施,但"应当重新进行实名核验,根据风险等级采取有区别的、相应的核验措施"。法律赋予的"区别对待"原则,在执行层面却异化为"一刀切"的懒政思维。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地区已开始探索差异化治理路径。上海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建立的"医疗行业白名单",将全市3.8万个医院工作电话纳入重点保护范围,通过专属模型降低误判率;广东省通信管理局推出的"急救绿色通道",允许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通过备案号码直接复机;浙江省实施的"分级处置机制",对中低风险号码采取短信提醒、限呼等柔性措施,而非直接停机。
这些创新实践印证了技术治理的另一种可能。正如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所言:"反诈不是技术竞赛,而是社会治理能力的综合考验。真正的智慧治理,应该让技术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技术。"
11月6日下午,在媒体介入后的第26天,杨先生终于收到中国移动的线上复机短信。这场漫长的拉锯战看似画上句号,却留下更深层的追问:当技术治理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如何避免其异化为冰冷的数字暴政?
答案或许藏在那些被忽视的细节里——杨女士手机里存着的37个患者随访记录,张先生手机相册中跨省调动的12张工作证,王女士微信里2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聊天记录……这些数字痕迹不是"涉诈证据",而是普通人努力生活的印记。
反诈之战的终极目标,是守护每个个体的安全感。这既需要技术模型的持续进化,更需要治理思维的范式转变:从"风险管控"转向"服务赋能",从"机械执行"转向"精准施策",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预防"。唯有如此,才能让技术治理真正成为温暖人心的力量,而非制造焦虑的源头。
当杨先生重新握紧恢复通讯的手机时,手术室墙上的时钟指向10:43。这个时刻提醒着我们:在数字治理的浪潮中,永远不要忘记技术为人服务的初心。毕竟,任何冰冷的算法,都抵不过一个鲜活生命跳动的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