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总统呼吁取消五常一票否决权 呼吁对联合国进行全面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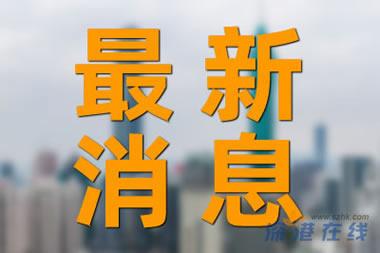
芬兰总统呼吁取消五常一票否决权
【芬兰总统呼吁取消五常一票否决权】9月24日,联合国大会第80届会议现场,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以一场充满火药味的演讲引发全球关注。这位新任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公开呼吁“取消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一票否决权”,并主张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成员国暂停投票权。这一提议直指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却意外触动了美国的核心利益,更将联合国70年未变的权力结构推向风口浪尖。斯图布的改革蓝图包含三大核心内容:彻底废除否决权:主张“任何单一国家都不应拥有凌驾于集体意志之上的权力”,认为否决权已沦为大国维护私利的工具;建立违规惩罚机制:若安理会成员发动“非法战争”或违反人道原则,应立即剥夺其投票权。此条款被解读为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扩大常任理事国席位:提议将五常扩至十常,新增席位分配给非洲(2席)、亚洲(2席)和拉丁美洲(1席),试图通过稀释现有五常权力实现改革。“当俄罗斯在乌克兰实施军事行动时,其否决权却能阻挠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这合理吗?”斯图布在演讲中质问。他特别提及2025年9月美国否决“加沙人道援助”提案的案例,直言“某些国家正将否决权变为保护盟友的遮羞布”。面对芬兰的激进提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9月26日的记者会上直言“过于天真”。他强调五常权力结构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并指出美国在过去一年中六次动用否决权均基于“国家安全利益”。数据显示,仅2025年9月,美国就否决了涉及加沙停火、人道援助的两项决议,其盟友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因此得以延续。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若按斯图布提出的“违规即停权”标准,美国自身早已触及红线。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2021年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导致的人道危机,均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认定为违反国际法。这种双重标准暴露出改革提议的内在矛盾:当芬兰试图用道德准则约束他国时,自身却难以经受同等标准的审视。
斯图布的提议并非孤立事件。2025年9月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提出限制五常否决权的三大方案:要求行使否决权时说明理由、对大规模暴行案件限制使用、建立联大审查机制。中美两国虽罕见表态支持改革,但在具体路径上存在根本分歧。
更深层的阻力来自《联合国宪章》的制度设计。根据宪章第108条,任何修改常任理事国权力的提案需经联大三分之二成员批准,且必须获得现任五常一致同意。这意味着只要有一个国家反对,改革便无法推进。历史上,安理会仅在1965年增加过4个非常任席位,此后50余年再无实质性变革。
“这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权力再分配的政治博弈。”国际关系学者李明指出,“五常不会主动削弱自身特权,发展中国家又缺乏足够筹码,改革注定陷入僵局。”
作为2023年新加入北约的国家,芬兰的改革提议被普遍视为向西方阵营递交的“投名状”。斯图布在演讲中明确表示:“如果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体系中得不到应有代表权,他们就会背弃这个机构。”这种将改革与发展中国家权益捆绑的论述,实则暗合美国拉拢非洲、拉美对抗中俄的战略需求。
俄罗斯对此反应强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嘲讽道:“某些国家试图用道德表演掩盖地缘政治野心,但联合国不是可以随意改写的剧本。”她特别指出,芬兰在提议中刻意回避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这种选择性正义暴露了改革的虚伪性”。
尽管遭遇重重阻力,联合国改革的需求已不容忽视。数据显示,2025年安理会在叙利亚、也门、乌克兰等热点问题上的决议通过率不足40%,否决权滥用导致国际危机应对机制近乎瘫痪。古特雷斯警告:“如果继续维持现状,联合国将失去解决全球性挑战的能力。”
发展中国家开始探索折中方案。法国自2015年起联合墨西哥推动“道德承诺倡议”,呼吁五常在重大暴行案件中自愿放弃否决权,已获103国联署。日本则提出渐进式改革:新增常任理事国在15年内放弃否决权,期满后再议。这些方案虽未触及核心矛盾,但为僵局提供了可能的突破口。
芬兰总统的激进提议,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巨石,激起了关于全球治理未来的深刻反思。当否决权从二战时期的“大国协调机制”异化为“私利保护工具”,当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碰撞日益激烈,国际社会需要的不是非黑即白的站队,而是基于规则的理性对话。正如古特雷斯所言:“改革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让现有机制更适应时代需求。”在这场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弈中,唯有超越零和思维,在维护战略稳定与推动民主化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避免联合国沦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毕竟,这个承载着78年和平愿景的机构,其存续本身已是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