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捡菌子 一抬头黑熊呲牙站面前 村民冒雨搜救10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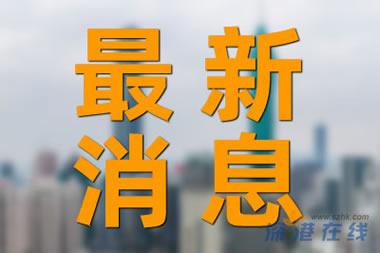
男子捡菌子 一抬头黑熊呲牙站面前
【男子捡菌子 一抬头黑熊呲牙站面前】9月20日下午2时许,重庆市城口县高楠镇岭楠村村民李先生在渝陕交界的大巴山深处遭遇黑熊袭击,左脚被咬伤、腰脊椎多处骨折,这场突如其来的野兽袭击事件,让这个以采菌为生的村庄陷入震动。当日清晨,连绵阴雨让大巴山的松林笼罩在薄雾中。李先生与妻子背着竹篓、手持弯刀,像往年一样进山采菌。“最近雨多,鸡枞菌、牛肝菌长得旺,一天能卖三四百元。”妻子回忆,丈夫走得快,她落在后面约200米。下午2时,当李先生在坡坎边弯腰捡菌时,抬头猛然发现一头约200斤重的黑熊正站在下方,张嘴露出獠牙,发出低沉的咆哮。“它冲上来咬住我左脚的水鞋,用力一甩就把我摔下坡坎。”李先生回忆,坡坎高约5米,坡度近70度,他跌落时撞到一棵碗口粗的松树才停下,但已昏迷。妻子在林间呼喊丈夫无果后,循着野兽吼声找到坡坎下,发现丈夫左脚水鞋失踪,小腿上有两处齿痕,鲜血浸透裤管。“黑熊可能还在附近,我们不敢轻举妄动。”李先生苏醒后,强忍剧痛与妻子躲到一处低洼地带。他们试图拨打110求救,但密林深处手机毫无信号。下午4时,李先生借着微弱信号联系到村民刘某,称自己“被黑熊咬伤,跌落山崖”。岭楠村村主任杨运平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20余名熟悉地形的村民进山。“我们带了弯刀、绳索和简易担架,但最棘手的是定位。”杨运平展示的救援轨迹图显示,李先生所在位置处于渝陕两省交界处,手机定位在3平方公里范围内波动,“林中根本没有路,我们用弯刀砍出临时通道,每走100米就要核对方向。”当晚7时,暴雨突至。村民们穿着雨衣,在能见度不足5米的林间摸索前行。“李先生的呼救声越来越弱,我们只能靠手电筒光柱扫射。”参与救援的村民王建国说。经过3小时跋涉,救援队终于在山洼处发现蜷缩在树下的夫妻俩——李先生因失血过多面色苍白,妻子用外套为他包扎伤口,自己却浑身湿透。
“他摔伤严重,不能背,只能搀扶着走。”杨运平描述,众人用松枝和藤条制作简易担架,但李先生每移动半米就痛得抽搐,最终改为两人架着胳膊、三人托着臀腿的“人肉搬运”。午夜时分,当救援队将伤者抬出山林时,20把弯刀已砍断17把,所有人的手掌都磨出血泡。
“这不是今年第一起黑熊伤人事件。”高楠镇林业站站长张明透露,2023年以来,该镇已记录12起黑熊活动报告,其中3起涉及村民财产损失。2025年8月,有村民发现黑熊偷食蜂箱,蜂蜜损失超50斤。
生态专家指出,大巴山自然保护区黑熊数量从2010年的不足30头增至2025年的80余头,种群扩张导致栖息地与人类活动区重叠。“黑熊是杂食性动物,但秋季为储备冬眠脂肪,会加大高热量食物摄取。”西南大学野生动物保护教授李峰分析,野生菌、蜂蜜等山货正成为黑熊的“秋季补给站”。
“医疗费已由野生动物受害险报销。”城口县林业局负责人介绍,2021年该县在重庆率先推出野生动物致害政府救助责任保险,2023年将保障范围扩大至熊、野猪、猕猴等12类保护动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提升至每人3万元。李先生的住院清单显示,其7.8万元医疗费中,保险公司承担90%,个人仅支付7800元。
但更深层的矛盾仍在发酵。岭楠村村民大会上,63岁的赵大娘抹着眼泪说:“我孙子去年被野猪拱伤,现在看到山货都不敢捡。”数据显示,城口县2025年野生菌产量同比下降40%,部分村民转而种植中药材。“生态保护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人的安全账。”村民王德发的话引发全场沉默。
站在李先生跌落的山崖边,松针上的血迹已被雨水冲刷干净,但竹篓里散落的鸡枞菌仍在诉说这场悲剧的荒诞——人类为谋生进山,野生动物为觅食下山,两个物种的生存轨迹在密林中激烈碰撞。
城口县的探索提供了启示:从2016年首例黑熊伤人事件后的手足无措,到如今形成“保险理赔+生态补偿+安全教育”的防护网,这个大巴山深处的小镇正在寻找人与自然的平衡点。但更根本的解决方案,或许在于重新审视“靠山吃山”的传统模式——当野生动物保护进入深水区,我们是否该为山区居民开辟更多元化的生计?
目前李先生已完成腰椎手术,生命体征平稳。病房窗外,连绵秋雨仍在冲刷着大巴山的褶皱,那里既有野生菌破土而出的生机,也藏着黑熊徘徊林间的阴影。这场人与自然的博弈,远未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