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粪“围村”成养殖大县最头疼的事 肉牛养殖蓬勃发展,粪污激增带来新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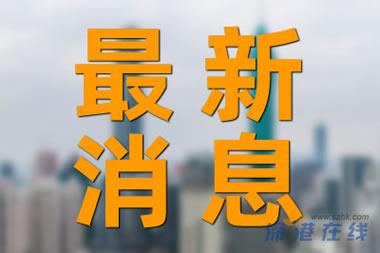
牛粪“围村”成养殖大县最头疼的事
【牛粪“围村”成养殖大县最头疼的事】近期,随着肉牛出栏量突破2200万头大关,我国肉牛养殖业迎来蓬勃发展期。然而,在东北、华北等养殖大县,一场由牛粪引发的生态危机正悄然蔓延——村路两侧、田间地头、壕沟林带,甚至村民房前屋后,大量未经处理的牛粪堆积如山,形成“牛粪围村”的怪象。这场危机不仅威胁农村人居环境,更暴露出我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体系的深层短板。在东北某肉牛饲养量达70万头的养殖大县,村路两旁的牛粪堆高达两米,夏季高温下,刺鼻的腐臭味弥漫数里。村民王大爷无奈地说:“以前水塘能养鱼,现在粪污渗进去,鱼全死光了,连洗衣服都不敢去。”类似场景在河北、内蒙古等地屡见不鲜:某村集体大坑被填满牛粪,污水渗透导致周边农田减产;另一村因粪污堆积引发蚊蝇滋生,儿童感染肠道疾病比例同比上升30%。一头肉牛每年产生5-6吨粪污,一个千头规模的养殖村年产粪污可达数千吨。然而,多数村庄的粪污收集点形同虚设——某村耗资20万元建设的百平方米收集站,因容量不足、运输困难,最终沦为“摆设”,养殖户被迫将粪污倾倒至偏僻角落。这种“治理-反弹-再治理”的恶性循环,让基层干部叫苦不迭:“执法部门追责时,我们只能默许村民偷倒,否则粪污会直接堆到村委会门口。”
尽管畜禽粪污发酵还田被公认为最佳解决方案,但现实中的多重障碍让这一技术难以落地。在山东某产粮大县,种粮大户老潘算了一笔账:收集6000立方米粪污需投入3.6万元购买扬粪机,运输成本1.5万元,加上堆沤、还田等环节,每公顷土地处理成本高达800元。而另一位大户老常虽通过粪肥还田实现玉米增产1000斤,但其示范效应仅覆盖周边3个村庄,多数村民仍因“怕麻烦、嫌脏”拒绝参与。
有机肥企业的困境更凸显产业链断层。山西文水县扶农生物科技公司虽建成11座中转站,年处理粪污150万吨,但2025年有机肥销量同比骤降85%,仓库积压2万吨产品。企业负责人坦言:“前几年每吨有机肥能卖400元,现在300元都没人要,只能暂停收购粪污。”这种“企业无利可图—收集体系瘫痪—粪污无处可去”的死循环,正在全国多地上演。
面对困局,部分地区已探索出可行路径。宁夏泾源县龙潭村通过“散户养殖+集中托管+粪污利用”模式,建成2处养殖示范区,配套有机肥加工车间,将牛粪转化为每立方米60元的高附加值产品,带动161户养殖户年均增收超万元。村支书冶浩天自豪地说:“去年光卖牛粪就挣了24万元,现在周边村子抢着送粪上门。”
政策创新同样关键。黑龙江嫩江市出台《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三年行动方案》,对粪污堆沤点建设补贴50%,并建立“养殖户+合作社+种植大户”利益联结机制,使粪污还田率提升至75%。山西文水县则将粪污治理纳入“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入企业建设深加工中心,将粪污转化为生物质燃料,年替代标煤12.8万吨。
牛粪围村现象,本质上是传统养殖模式与生态文明要求的激烈碰撞。当养殖业成为县域经济支柱,当“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出现矛盾,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任何产业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破解这一困局,需要政府、企业、农户形成合力:建立“县-乡-村”三级粪污收储运体系,降低处理成本;通过碳交易、绿色信贷等市场机制,提升有机肥企业积极性;将粪污资源化利用纳入村规民约,激发村民主体作用。正如中国农科院专家所言:“每公顷土地实施25立方米粪肥还田,可少施化肥600斤、增产1000斤,综合效益超2000元。这不是负担,而是待挖掘的‘绿色金矿’。”站在乡村振兴的历史关口,牛粪围村既是挑战,更是契机。当粪污变“绿金”、当臭味化清香,我们终将证明:生态与效益从不对立,绿色发展才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场破局之战,考验的不仅是技术与管理,更是一个民族对可持续发展的智慧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