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鬼”杨彬 任上被查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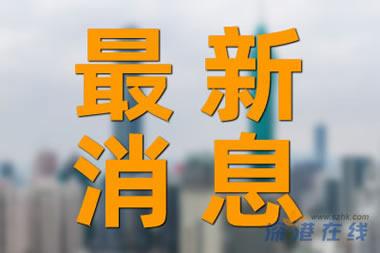
“内鬼”杨彬 任上被查
【“内鬼”杨彬 任上被查】9月10日,一则通报在纪检监察系统引发震动:河南省南阳市纪委监委宣布,郑州市纪委监委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纪检监察组组长杨彬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位曾以“监督者”身份出现在廉政会议上的女干部,最终成为被监督的对象,其职业生涯的戏剧性转折,撕开了纪检监察系统自我革命的深刻命题。根据公开履历,杨彬自2003年参加工作后长期深耕纪检监察领域。2019年,她已担任郑州市纪委监委驻市人社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并在2025年2月12日郑州市人社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以“监督者”身份通报全年案件查办情况。镜头前的她神情肃穆,强调“要推动责任向基层延伸”,而如今曝光的违纪违法事实,让这场廉政宣讲沦为黑色讽刺。值得注意的是,杨彬案并非孤立事件。2023年9月,南京市江宁区委原常委、区纪委原书记杨彬(与本案主角同名)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中纪委官网曾以“纪检监察系统干部教育整顿”为背景,将该案作为典型案例通报。两起案件虽无直接关联,却共同折射出纪检监察队伍中“灯下黑”问题的顽固性。杨彬案的调查权归属颇具深意——由南阳市纪委监委而非郑州市本级机构执行。这种“异地管辖”模式,直指地方纪检监察系统可能存在的利益关联。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纪检监察干部,上级纪委可指定其他地区纪委审查调查,以避免人情干扰。
“异地调查就像一把手术刀,能精准切割地方权力网络中的腐败病灶。”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分析,近年来多起纪检监察干部落马案均采用此模式,如2024年湖南省纪委监委对湘潭市纪委原书记胡卫兵的调查,同样由异地纪委负责。这种制度设计,既是对“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实践回应,也彰显了中央刀刃向内的决心。
杨彬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25年2月的廉政会议上。据郑州市人社局官网报道,会议播放了警示教育片《清风正好扬帆》,杨彬在发言中强调“要分析案发特点,提出明确要求”。这种“台上讲廉政、台下搞腐败”的荒诞场景,被网友戏称为“廉政会议上的表演艺术家”。
“形式主义是腐败的温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指出,部分纪检监察干部将廉政会议视为政治秀场,满足于留痕管理而非实质监督。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查处形式主义问题1.2万件,其中37%涉及廉政教育走过场。杨彬案暴露的,不仅是个人道德沦丧,更是某些地方纪检监察工作的机制性漏洞。
杨彬落马恰逢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进入深水区。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5年以来已有43名纪检监察干部被查处,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占28%。这些数据背后,是“清理门户”的雷霆之势:技术赋能监督:多地纪委监委建立干部廉政档案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房产、股票等异常财产变动;家风建设强化: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家属签署《廉洁承诺书》,将监督触角延伸至“八小时外”;轮岗制度完善:对派驻机构负责人实行五年任期制,避免长期驻点形成利益共同体。
“纪检监察机关不是‘保险箱’,纪检干部更没有天然免疫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负责人表示,杨彬案再次证明,对执纪违纪者的零容忍,是对纪检监察队伍最大的保护。
杨彬案引发的舆论风暴中,“破窗效应”理论被反复提及。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当纪检监察系统出现“内鬼”,其对公信力的损害远超普通腐败案件。
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制度与文化的双重变革。一方面,要完善纪检监察权力运行制约机制,如推行案件查办分离制度,避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另一方面,需培育“监督者必须接受更严格监督”的组织文化,让“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口号转化为行动自觉。
杨彬的办公室里,那枚刻着“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徽尚未蒙尘,而她的人生轨迹已划出污点。这起案件给所有纪检监察干部敲响警钟:当监督者失去监督,权力必然走向异化;当廉政宣讲沦为表演,公信力终将崩塌。
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今天,纪检监察队伍的自我革命没有休止符。唯有以更严格的制度约束、更彻底的思想洗礼、更无畏的刀刃向内,才能回答好“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时代之问。杨彬的陨落不应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应成为净化政治生态的又一块奠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