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华裔数学家被迫在美筹款 科研经费断供,紧急筹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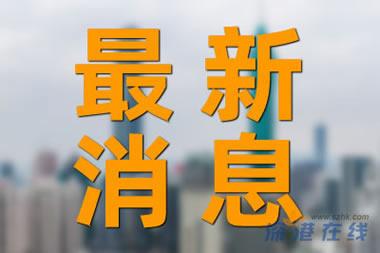
顶尖华裔数学家被迫在美筹款
【顶尖华裔数学家被迫在美筹款】近日,美国科研界被一则消息震动:50岁的菲尔兹奖得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数学系教授陶哲轩,因联邦科研经费断供,不得不放下数学研究,为纯数学与应用数学研究所(IPAM)四处筹款。这位被《华盛顿邮报》称为“数学界莫扎特”的学者,正经历着职业生涯中前所未有的困境。事件起因可追溯至7月31日。特朗普政府以UCLA“未能营造无反犹太主义和偏见的研究环境”为由,冻结该校约5.84亿美元联邦研究资金,其中涉及NSF对IPAM的资助。尽管法院于8月12日裁定恢复拨款,但陶哲轩透露,截至9月初,他个人及IPAM的资助仍无法发放,而研究所的储备金仅够维持数月运营。“过去两周,我一直在与捐赠者会面,IPAM的生存已进入倒计时。”陶哲轩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坦言。作为NSF资助的核心项目,IPAM自2000年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数学家、工程师与工业界的跨界合作,其成果甚至应用于提升核磁共振扫描速度。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资金危机,让这个年运营成本超千万美元的机构陷入瘫痪。陶哲轩的困境并非孤例。根据NSF的2026财年预算提案,特朗普政府计划将NSF预算削减57%,同时大幅削减气候研究、公共卫生等领域的支出。这种“政治优先级替代同行评议”的拨款逻辑,正引发连锁反应:科研机构动荡: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联合1900名学者发布公开信,警告政府“拆解联邦科研机构、解雇数千名科学家”的行为,正在摧毁美国科研的根基。环保署3天内停职140名签署抗议信的员工,进一步加剧了学术界的恐惧。
人才逆向流动:据《自然》杂志调查,75%的受访美国科研人员考虑离开,欧洲和加拿大成为首选目的地。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个月,美国科研人员海外求职申请量同比增长32%。欧盟迅速推出5亿欧元“选择欧洲科研”计划,法国、澳大利亚等国也纷纷抛出橄榄枝。
基础研究边缘化: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汝鹏指出,特朗普政府将科研与产业政策深度捆绑,人工智能等“效用科学”获得优先扶持,而数学、理论物理等基础领域则面临审查与经费削减。这种短视政策正动摇美国科技创新的基石。
面对危机,陶哲轩选择站到台前。他不仅在NBC采访中直言“本届政府改变科学生态的激进程度超过第一任期”,更以实际行动呼吁改革:
筹款突围:陶哲轩通过个人影响力联系校友、企业及基金会,试图为IPAM争取过渡资金。他强调:“NSF资助不仅支持研究生参会,更让他们能暂停教学专注研究。这些年轻人是科研的未来。”
学术自救:在凤凰网专访中,陶哲轩透露正探索“大数学”模式——利用人工智能和协作平台,将复杂问题分解为可众包的任务。他以20年前解决MRI图像重建问题的经历为例,说明数学与现实需求的紧密联系:“当假币称重问题的解法被用于医疗影像处理时,基础研究的价值便显现无遗。”
生态警示:陶哲轩将政策突变比作“温度忽高忽低的房间”:“即使最终恢复适宜温度,人们仍会因担忧反复而无法安心工作。”这种不确定性,正迫使越来越多学者重新规划职业生涯。
历史总是充满讽刺。80年前,罗斯福政府通过《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确立科研国家战略,吸引全球人才涌入美国;80年后,特朗普政府的“反科学风暴”却可能引发人才逆流。曼彻斯特大学研究员基伦·弗拉纳根警告:“美国科学体系的稳定性已不再有保障。”
这场危机背后,是更深层的范式转变。当欧盟、中国等经济体加大科研投入,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呈现多点突破态势,全球科研版图正从“美国中心”向“多极化”演进。陶哲轩的困境,恰是这一转型期的缩影。
“我以前从未想过离开美国,但现在必须考虑所有可能性。”陶哲轩的这句话,道出了无数科研工作者的心声。科学探索本应超越国界与政治,但当政策成为枷锁,当经费化作筹码,学者们不得不为生存而奔走。这场危机终将过去,但它留下的警示值得深思: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不仅取决于资金与人才,更取决于对知识价值的敬畏、对学术自由的守护。正如陶哲轩在筹款信中所写:“数学不会因资金中断而停止,但人类的智慧需要土壤与阳光。”愿这场风暴过后,全球科研生态能迎来更理性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