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震惊!上海交大博士招生人数或超本科 3年扩招40%,2026年计划招生5000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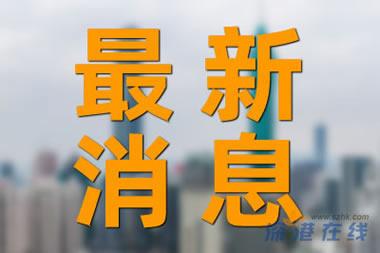
上海交大博士招生人数或超本科
【上海交大博士招生人数或超本科】博士头衔的光环正在数字膨胀中变得模糊,上海交大的博士招生量已超过美国前20所大学的三分之一。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发布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其中提到2026年博士研究生计划招生规模5000名左右,事件引发网友讨论。据悉,三年时间,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的扩招幅度已然突破40%大关。据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网官网发布的招生简章信息,2026年该校计划招收博士研究生约5000名,其中校本部计划招生规模约为4000名。学校会依据学科建设实际需求以及生源状况进行灵活调整,最终的招生规模将以教育部正式下达的招生计划文件为准。在培养形式方面,学习形式分为全日制与非全日制两种。其中,直博生的基本学习年限设定为5年,其他类别博士生的基本学习年限则为4年。此外,该招生简章也对选拔方式、申请条件、申请及考核流程等共计14项进行了说明。11月5、6日,记者多次拨打招生办电话未果,宣传部门人员称会了解但截至发稿未回复。上海交大博士招生5000人,超哈佛3倍多,达美国前二十高校年博士毕业生总和的三分之一。博士招生规模膨胀非交大独有,2019年起博士扩招年均1.5万人,2025届毕业生已超15万,较五年前增217%。
博士扩招的背后,是严峻的就业形势。当本科已成为普通教育,硕士逐渐普及,研究生教育的层次正在被重新洗牌。
有观点认为,博士扩招已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缓冲器。“博士扩招,不是培养科研精英,而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这样的声音在网络上屡见不鲜。现实中,就业市场的冰冷数据令人心惊。在今年9月举行的“黑龙江省人才周”招聘会上,有11万2423名毕业生涌入会场,却面对仅有9000余个岗位的残酷竞争。即使是中国顶尖院校的毕业生,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更让人心寒的是,即使博士毕业,也可能只能去图书馆做月薪4000元的工作。哈尔滨那鹅毛大雪的冬天很冷,恐怕也没有就业市场那股寒風更让毕业生们心寒。
博士数量的激增,并没有带来科研创新的跃升,反而让博士教育在“量变”中逐渐走向“贬值”与“变质”。培养一个博士,需要项目、经费、论文、导师指导、学术积累,每一步都离不开时间与精力的投入。但当招生数量成倍增长,而导师与科研资源并未同步增加,博士教育就被迫“标准化”“模板化”“流程化”。导师带十几个博士已成常态;研究课题被反复拆分;论文选题高度雷同,创新空间越来越小。博士培养从“研究”变成了“产出”,从“学术训练”变成了“学历供给”。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数据,十年来中国专任教师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4%。上交大大量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同时,是否有足够的博导老师支持,不由令人打个问号。同时,高等院校的就业承载力明显不足。双一流高校招聘门槛已抬高至“海外经历+顶刊论文+院士推荐”,北京某顶尖学府63%的青年教师候选人持有院士推荐信。
博士扩招还面临着结构性矛盾。虽然招生规模扩大,但并非所有学生都能按期完成学业。根据数值推算,大约只有75%的学生能够顺利毕业,其余25%可能面临延期毕业、中途退学或其他未完成学业的情况。
这一差异反映了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学术挑战和淘汰机制。培养目标与市场需求脱节也是突出问题。63%的高校未开设应用型博士课程,仍以传统学术训练为主。当华为、商汤科技等企业急需“技术攻关型博士”时,多数毕业生却只具备论文写作能力,导致“企业招不到人,博士找不到岗”的错位。“唯论文”导向下,博士生沦为“学术流水线工人”。某985高校理工科博士平均每周实验时间超80小时,却鲜有机会参与产学研转化,这种培养模式造就的“论文高手”,在企业看来实为“能力跛脚”。
博士数量超过学术界承载能力并非中国特有现象。过去几十年,全球博士教育经历了高速增长。在属于经合组织的38个国家中,从1998年到2017年,新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仍在持续增加。但学术界的就业岗位数量跟不上博士生数量的增长。继续读博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接受“学者”、“科研人员”的思维训练,在和其他面向非学术界的毕业生进行竞争时,优势并不大。2023年对英国4500多名博士毕业生的一项研究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博士毕业生在学术界之外就业。这种就业趋势可能意味着毕业生从事的不是基于研究的工作,相当于“转行”从事专业领域之外的工作。
破解博士文凭贬值困局,需构建“供需适配、评价多元、流通顺畅”的新生态。上海交大等顶尖高校应承担起范式转型的引领责任。招生的精准调控机制是第一步。建立“岗位预测—动态调整”体系,参照国家战略产业(如芯片、生物医药)的人才缺口确定招生规模。德国的经验可资借鉴:其博士招生与企业研发项目直接挂钩,巴斯夫集团每年联合高校培养200名“工业博士”,就业率达100%。同时,培养模式需要跨界重构。推行“学术+应用”双轨制,每位博士生配备学术导师与产业导师,要求30%的培养时间用于企业实践或政策研究。东北某高校的数据证明,具备产学研转化经验的博士录用率是纯学术型人才的2.3倍。许多研究人员都在呼吁“重新评估”博士学位的用途,并对高等教育体系进行改革,以适应博士生职业格局的变化。一些国家,如日本、德国和英国,已经开始做出改变,例如在博士学习期间为学生提供培训和带薪实习,或者提供“工业博士”等替代方案,让学生与公司合作开展研究。
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膨胀速度,比货币贬值的速度还快。当三线城市职业技术学院都能吸引海归博士竞聘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博士头衔已从稀缺标签蜕变为基础性配置。真正的竞争已从学历的竞争转向知识变现能力的较量。教育的价值,不在于培养多少博士,而在于培养出多少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