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称子宫被装监听器起诉医院 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请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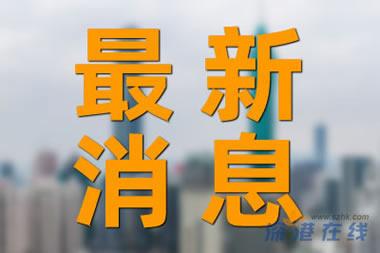
女子称子宫被装监听器起诉医院
【女子称子宫被装监听器起诉医院】近日,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特殊医疗纠纷作出终审判决:驳回59岁女子叶某关于“医生在其子宫内安装监听器”的索赔诉求。这起持续数月的诉讼,因原告将妇科常见囊肿误认为电子设备、法院两审均以“证据不足”驳回请求而引发广泛讨论。案件背后,折射出公众对医学影像的认知偏差、精神健康问题的隐蔽性,以及法律“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刚性约束。据叶某自述,2016年她在绥中县某医院接受宫内节育器取出术后,长期感到腹部不适。2025年1月,她在另一家医院进行彩超检查,结果显示“左附件区存在约2.7×2.4厘米囊性回声,盆腔少量积液”。叶某声称,近两年通过手机播放歌曲时,能感知到体内存在异物,并据此断定该囊性回声为医生私自安装的“监听器”。“医生在手术时未经我同意放了东西,这肯定是侵犯隐私!”叶某在起诉书中要求医院免费取出“监听器”,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然而,她的指控从一开始就面临医学层面的质疑。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专家杨晨光指出,超声检查中的“囊性回声”本质是声波遇到不同密度组织后的反射信号。人体内液性成分(如卵泡、黄体囊肿)通常呈现“无回声”或“囊性回声”,而金属或电子元件构成的“监听器”则会显示为边界清晰、密度均匀的强回声区,并伴有典型“声影”特征。“将囊性回声误认为监听器,相当于把月亮认成飞机。”杨晨光比喻道。现代彩超技术已能清晰区分生理性结构与外来异物,叶某的检查报告明确标注了囊性回声的大小、边界和形态,这些特征与电子设备在超声影像中的表现截然不同。更关键的是生理结构限制。子宫腔是容积仅5毫升的密闭肌性器官,任何外来异物都会引发剧烈疼痛、出血或感染。叶某自称“体内有监听器”多年却无相关症状,从医学机制上难以成立。
一审法院审理发现,叶某的指控存在两大核心漏洞:客观证据缺失:彩超报告未显示子宫内存在电子设备,叶某将囊性回声等同于“监听器”缺乏事实依据;因果关系无法证明:即使存在异物,叶某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表明该异物与2016年的节育器取出术有关。
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叶某需承担举证责任。然而,她既未申请医疗损害鉴定,也未提供手术记录、器械清单等直接证据。反观医院方,提交的彩超报告、病历资料等形成了完整证据链,证明诊疗过程符合规范。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时强调:“叶某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监听器’存在,亦无法证明其与医院手术有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这一判决与福建男子林某案形成对比——林某因怀疑邻居安装窃听器而杀人,最终被鉴定为“偏执性精神障碍”获判死缓。两起案件的共性在于,当事人均将主观妄想当作客观事实,且无法提供有效证据。
心理咨询师黄坤强指出,叶某的“监听器妄想”可能是焦虑情绪躯体化的极端表现。中老年女性在更年期前后,激素水平波动易引发情绪不稳,若叠加对医疗行为的不信任、对衰老的恐惧等心理因素,就可能将生理上的轻微不适放大为“被侵害”的妄想。
“约60%的抑郁症患者会出现身体疼痛,40%的焦虑症患者伴有胸闷、心悸等症状。”黄坤强透露,这类躯体化症状往往缺乏明确生理病因,是心理压力通过身体不适表现出来的防御机制。叶某的案例中,长期焦虑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引发肌肉紧张、感知异常,进而强化“体内有异物”的错误认知,形成“情绪不适→躯体感受→认知偏差→情绪更糟”的恶性循环。
这起闹剧给公众带来三重启示:医学认知需科学:超声检查中的囊性回声是极为常见的生理现象,盲目将其与电子设备关联,暴露出公众对医学影像技术的误解;法律维权讲证据:在医疗纠纷中,患者需通过医疗损害鉴定、专业机构检测等手段固定证据,仅凭主观猜测难以获得法律支持;精神健康应重视: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不适,且多次检查无明确病因时,需考虑心理因素的可能。及时寻求心理咨询或精神科帮助,比反复做生理检查更有意义。
目前,叶某的腹部不适已被确诊为卵巢囊肿,医生建议定期复查。这起案件虽以败诉告终,却为全社会敲响警钟: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既要相信医学检测的客观性,也要倾听身体背后的心理诉求。唯有让科学驱散误解,用关怀化解焦虑,才能避免“想象中的伤害”成为现实中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