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中小学班级人数为何不减反增 约16.8%的班级学生数达到或超过28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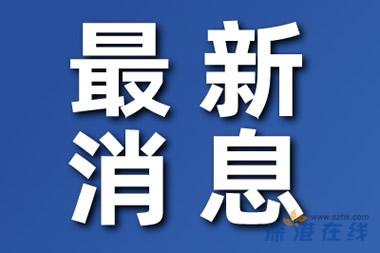
韩国中小学班级人数为何不减反增
【韩国中小学班级人数为何不减反增】9月14日,据报道,在韩国生育率持续低迷、学龄人口同比减少2.3%的背景下,该国中小学班级规模不降反增,约16.8%的班级学生数达到或超过28人,较2024年上升0.3个百分点。这一数据与韩国教育部2022年提出的“班级规模不超过28人”计划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这个东亚发达国家在人口结构剧变中的深层教育危机。根据韩国教育部9月11日发布的最新数据,首都圈成为“班级超载”重灾区。在京畿道光州市,初中班级中达到28人以上的比例高达87.7%,金浦、果川、华城等卫星城相应比例均超80%;首尔江南区作为精英教育聚集地,初中、高中超载班级占比分别达78.1%和51.3%;旅游胜地济州岛的初中超载率也攀升至48.7%。更值得警惕的是学段分布失衡。尽管小学超载班级占比从2024年的4.56%降至2.83%,但初中、高中超载率分别从34.7%、25.5%激增至38.8%、25.7%。这种“初中塌陷”现象与学龄人口结构直接相关——截至2025年4月1日,韩国小学年龄段人口同比减少6%,而初中年龄段人口反而增加2.8%,形成独特的“橄榄型”学龄人口分布。“每个超载班级背后,都是师资力量的捉襟见肘。”首尔教育大学教授李敏浩指出。教育部数据显示,2025年韩国在册教师总数为50.61万人,同比减少0.6%。其中小学教师减少1.8%,高中教师减少0.9%,仅初中教师微增1.1%,但增幅远不及需求增长。以京畿道为例,该地区初中班级超载率高达58.6%,但教师数量仅增加0.9%,导致平均每位教师需承担更多教学任务。
这种矛盾在首尔江南区尤为突出。作为韩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聚集地,该区初中超载率达78.1%,但教师编制增长不足1%。某重点中学教师金女士透露:“我们不得不将原本计划开设的选修课改为大班授课,甚至取消了部分实验课程。”这种“缩水版”教育模式,正在动摇韩国“教育立国”的根基。
韩国教育部的困境,折射出政策制定与现实脱节的深层问题。2022年,为应对生育率下滑,教育部推出“小班化改革”,计划通过三年时间将班级规模控制在28人以内。然而,该政策未充分考虑学龄人口分布的“时间差”——当前初中生源激增源于2012年左右的生育小高峰,而政策制定时却以总人口萎缩趋势为依据。
更严峻的是财政投入的滞后性。韩国教育开发院报告显示,2025年教育预算中,师资培训经费仅占1.2%,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3.5%的水平。在仁川市某中学,校长不得不自筹资金聘请临时教师:“我们向家长会募捐,用筹到的钱支付代课老师工资,这在全国已不是秘密。”
这场教育危机正在引发连锁反应。在济州岛,超载班级导致学生人均活动空间从1.2平方米压缩至0.8平方米,部分学校被迫取消课间操;在釜山,家长们自发组织“班级规模监督团”,要求教育局公开教师分配细则;甚至在野党也抓住这一议题,在国会质询中直指文在寅政府时期的教育政策“忽视人口结构剧变”。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人才储备的萎缩。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2023年新生儿数量降至23万人,创历史新低。按照当前趋势,到2040年韩国中小学在校生将减少至350万人,仅为2020年的一半。“当教室逐渐空置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学生,更是国家的未来。”首尔大学社会学家金昌锡的警告,正在成为现实。
面对困局,韩国教育界开始探索结构性改革。在光州市,教育局试点“浮动编制”制度,根据学期初实际报名人数动态调整教师岗位;首尔江南区部分学校引入AI助教系统,通过智能批改作业减轻教师负担;更有教育专家提出“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构想,让优质课程突破班级边界。
“这不是简单的加减法问题。”李敏浩教授强调,“我们需要重建整个教育生态系统,从招生政策到教师培养,从课程设置到校园建设,都必须适应少子化时代的新常态。”这种转型的迫切性,在9月15日发布的《2025年全球教育竞争力指数》中得到印证——韩国排名较去年下滑3位,其中“教育公平性”指标跌出前十。
韩国遭遇的教育困局,实则是全球发达经济体的缩影。日本文部科学省数据显示,该国公立中小学平均班级规模已从1995年的32.1人降至2025年的26.8人,但偏远地区仍存在“1人学校”;德国巴伐利亚州通过“合并校区”应对生源减少,却引发社区文化断裂争议;新加坡则选择“精英化”路线,用高额补贴维持小班教学,但加剧了社会阶层固化。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在生育率下滑不可逆的当下,教育质量与公平的平衡木愈发难走。韩国教育副总理李周浩在9月14日的记者会上坦言:“我们正在用一代人的时间,经历其他国家半个世纪的人口变迁,这要求我们必须以超常规思维推进改革。”
当夕阳透过首尔某中学的窗户,照在挤满40名学生的教室里,黑板上“未来”二字的粉笔痕迹显得格外醒目。这场关于教育规模的争论,终将指向一个更深层的叩问:在人口结构剧变的浪潮中,一个国家如何守护每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答案或许不在教室的课桌排列中,而在整个社会对教育本质的重新认知里。
